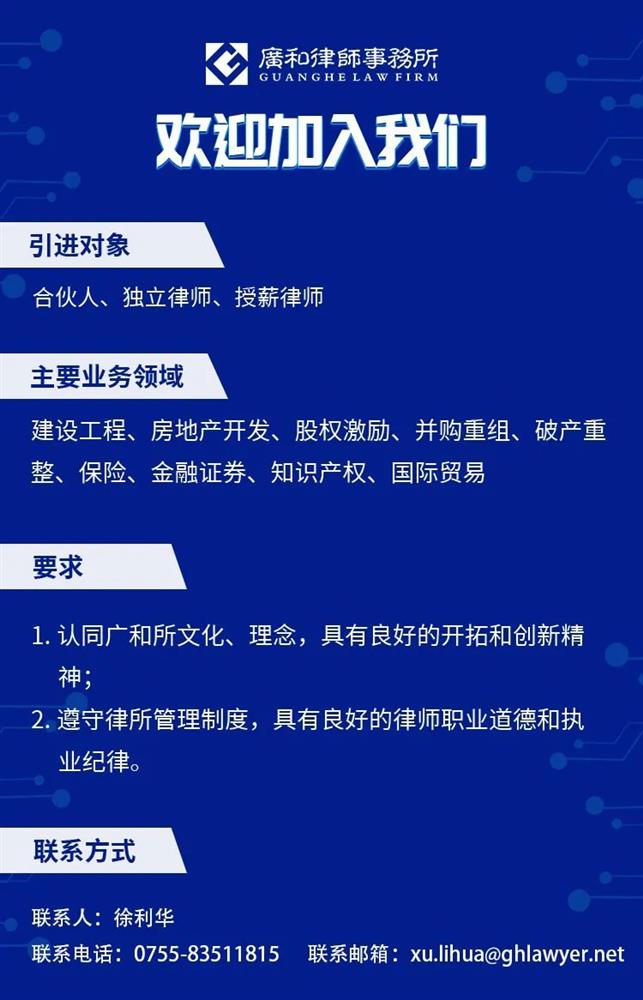夫妻婚姻存续期间,房屋份额登记在一方名下,登记方未经另一方同意转让房屋所有权份额的,登记方侵犯了另一方对房屋享有的共有权,受让方无权请求登记方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但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受让方可向登记方主张赔偿损失。
2004年3月22日,原告与被告作为共同购买方与开发商签订深圳市某房屋买卖合同,共同购买涉案房屋,后双方共同办理了涉案房屋的抵押贷款合同,原告负责偿还涉案房屋的银行按揭贷款。2004年6月,涉案房屋登记在原被告名下,原被告各站50%份额。涉案房屋由原告占用使用。2006年3月,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双方经过认真洽谈协商,自2004年3月22日起,被告同意将涉案房屋的50%所有权转让至原告,原告持有涉案房屋的100%份额并可自由全权处置涉案房屋。因被告一直没有配合原告将涉案房屋50%份额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原告遂于2016年8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协助将其名下的50%份额转移登记至原告名下。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系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法院认可其效力,遂支持了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将50%份额转移登记至原告名下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提出上诉,被告上诉主要理由之一是涉案房屋是被告与其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未经其配偶同意就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应认定无效,一审没有追加被告配偶作为共同诉讼参与人,违反法定程序。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配偶是否同意上述处分行为或是否追认上述处分行为与原告的诉请能否成立有关,一审法院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遂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
一审法院重新审理后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协议书》得到被告配偶的同意或事后追认,《协议书》归于无效,遂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该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原告认为《协议书》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签订《协议书》转让其房屋所有权份额的行为未经其配偶的同意,侵犯了其配偶对房屋的共有权,由于该共有权属于物权性质,相对于原告基于《协议书》请求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债权权利,物权权利具有优先性,故二审法院对原告请求办理过户登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同时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协议书》效力问题,被告的处分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但该《协议书》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一审认定《协议书》无效属于使用法律错误,二审予以纠正。一审法律适用错误,但是处理结果正确,二审遂维持了一审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
原告经历四轮诉讼程序,前后历时超过三年,可谓是一波四折,但最终结果却是法院没有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切回到了原点。原告对该最终判决结果是并不满意的,遂找到广和律师事务所,聘请广和律师为其进行维权。
广和律师综合分析后认为,虽然被告签订《协议书》之时并未取得处分权,但是并不影响被告订立《协议书》的债权行为效力,《协议书》依然合法有效,被告订立《协议书》后无法继续履行《协议书》必然导致原告相关损失,原告可以诉请被告赔偿损失。接受原告的委托后,原告向一审法院再次起诉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一审法院审理后支持了原告请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
婚姻存续期间,一方购买并登记在该方名下的房屋,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这点应无异议。实践中,确实存在出于各种目的,登记方未经配偶方同意,与第三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虽登记于该方名下但实际为夫妻共有房屋对外进行转让的现象。这种转让可能因相互之间的利益博弈而引发纠纷,即转让方或者转让方配偶试图实现不发生房屋转让进而保留房屋的结果,而受让方试图达到实现房屋发生转让的结果。通常一旦发生纠纷,无论是转让方配偶还是转让方,均会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为由主张权利或者予以抗辩;而受让方则通常会积极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以此实现各自诉讼目的。本案发生纠纷主要原因是,转让协议签订于2006年,十年之后深圳市的房屋市场价格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作为转让方的被告基于巨大利益考虑,不希望失去50%份额利益,而作为受让方的原告则是期望完成过户登记的,实现涉案房屋的全部利益。但是无论各方出于何种目的,终归是要回到无权处分情形下,房屋买卖合同效力问题上来。以本案为例,正常而言,作为房屋出卖人的被告负有交付涉案房屋并移转其所有权的义务,因此,被告应当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然而,被告在出卖涉案房屋之时,因涉案房屋50%份额系被告与被告配偶共同共有的,共同共有的处分权应当经共同共有人一致同意方可行使。但原告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取得被告配偶的一致同意,被告并无处分权,被告却订立《协议书》将涉案房屋对外进行转让,这就是较为典型的无权处分。其次,法律上对于无权处分的合同效力是如何进行规定的。原《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这是较早对无权处分所进行的法律规定。即未经权利人追认的,无权处分的效力是待定的,未生效的。原《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物权法对于无权处分的合同效力作出了修订,即涉及到不动产物权的变动,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的,合同成立即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条更直接明确规定了以无权处分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法院不予支持。买受人可以要求出卖人承担无权处分的违约责任或者损害赔偿。《民法典》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民法典》第二百一十五条承继了原《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如无特殊情形,合同成立即生效,不再沿用原《合同法》所规定的无权处分需经追认后方为有效。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法律规定的逐步变迁,无处分权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从最开始的效力待定,生效是例外到,现行的合同成立即生效,无效是例外。无处分权而订立合同的效力问题在法律上得到明晰,即无处分权下的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是有效的,除非违反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按照原《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买卖合同时,出卖人一定要享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出卖人才可以与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如果出卖人此时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这种情况下所订立的合同就是“无权处分”的合同,这种合同就不能生效。根据反对解释,合同不能生效,则合同归于无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出台之前,实践中是不乏认定无处分权所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本案发回重审后的一审法院就持该观点,即该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未经配偶同意,擅自签订《协议书》,且配偶明确表示不追认,《协议书》归于无效,认定主要依据在于《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而反对上述观点的孙宪忠教授则认为,订立合同是典型的债权行为,不是处分行为,更不是无权处分行为。合同成立之后,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了债权的法律关系,而不发生处分性质的物权变动。因为原《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造成了合同履行的结果规定成为合同成立的前提条件的情况,这是一种严重的本末倒置。将这一规则应用于实践,造成了没有所有权的出卖人订立的合同不能生效,故大量的预售合同都不能生效的消极后果。所以这个时候不让合同生效,无效的合同就不产生约束力,致使当事人违约不受法律制裁,这就造成了大量不诚信的行为。因此,孙宪忠教授的结论是当事人可以自由订立合同,合同成立即有效。本案发回重审之后的二审基本上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协议书》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就是有效的。不同的是二审认为被告签订《协议书》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而孙宪忠教授的观点认为处分行为应当是发生物权变动的行为,订立合同本身并不等同于物权的变动,仅仅为设立债权的行为。笔者持类似观点,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有房屋的,不存在法律规定无效情形的,合同有效,但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合同的订立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应当鼓励和保护当事人之间的缔约行为,法律不应当过于限制或者排除当事人的缔约自由。判断合同的效力同样应当遵守当事人意思自治,只要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效力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当事人没有取得所有权而订立合同所导致的结果是合同履行不能,实践中也有合同届时不能履行或者无法履行的情况。没有履行的合同,也不是都应该无效的。从诚信原则的角度看,绝大多数合同也应该是生效的。否则,擅自认定合同无效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连违约责任都无法追究。回归本案,若认定《协议书》无效,则原告无法追究被告履行不能的违约责任,一方面被告从不诚信的行为中获益巨大且无需为此承担任何的不利后果,相反原告的损失则是巨大的。因此,无论从维护交易安全角度,还是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角度,合同履行不能不等同于合同无效,合同有效是原则,无效是例外,应当予以区别对待。所以,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有房屋而签订的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但是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基于前述分析,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有房屋而签订的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但是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作为受让方如何进行权利救济?根据《协议书》约定,被告负有将涉案房屋50%份额转移登记至原告名下的义务,但因被告没有取得其配偶同意,即便被告同意继续履行,但被告也无法完成该转让行为,被告明显属于无法继续履行《协议书》。被告事实上也无法实现所有权的转移,明显构成违约,作为守约的原告有权主张解除合同,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赔偿其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及《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七条“因出卖人未取得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的,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关于损失部分的赔偿范围,原《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已经对损失范围作出了相对明确的规定。唯一的难处在于如何理解可得利益。可得利益是指合同在完全履行以后,当事人可以实现和取得的财产利益,它具有未来性、一定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等特征。作为一种未来的利益,其在违约行为发生时并没有被当事人所实际享有,而必须通过实际履行才能得以实现;而只要合同如期履行,该利益就可能被当事人获得,故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因可得利益系未来可能获得的利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应受可预见规则的限制。本案中,原告另行起诉主张的损失是合同完全履行之后未来所能够获得的利益,即房屋上涨后的增值利益或者差价损失,该利益是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以及可预见性的。该利益正是基于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的增值利益无法实现,故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赔偿。但是对于该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时间节点,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争议,应当综合具体案情采取最具说服力的计算时间节点,以取得法院的采信,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
在房屋买卖交易过程中,作为买受人的一方在订立此类房屋买卖合同之时,务必尽可能明确转让方是否存在共有的情形以及其他影响转让方完成转移登记的因素,若存在,需排除未来合同履行不能的风险,并明确所有权转移不能的违约责任及损失赔偿计算依据。
若风险确实发生了,即在现行法律明确规定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处分权,物权不发生变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下,买受人作为理性的房屋购买人,应对合同无法履行可能导致的损害结果具有合理的预估,买受人需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保留相关证据,及时主张权利。